最重要的事不会成为新闻。它们发生时往往无声、微小,而新闻不过是“重大事件”经历了漫长蛰伏后的爆发时刻。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来说,上世纪70年代,就是一个“悄然无声”的变革开端。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放缓,美国工业生产下滑了14%。彼时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重获主导,哈耶克主义开始盛行,美国各半导体公司盈利受损,受市场所限,放缓了对新技术的投资。
而同样经济受挫的日本,却开启了一场逆势反超。
如今,日本人总爱把“古き良き时代”(逝去的美好时代)一词挂在嘴边。当他们说起这个词时,脑海中有一幅共同回忆: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昭和后半期。
在那段痛并快乐着的岁月,日本人有强烈的目标感:他们亟需一场战后废土中的复兴。外部条件也相对有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扶持日本,日本陆续以低价引进了美国最新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技术,打下了日后发起冲刺的基础。
到70年代,日本已创建了“官、学、研”一体化的产业发展制度,采取了闷声追赶的“举国模式”。
日本要举国重点攻克的领域,正是半导体。
1974年,石油危机后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就批准了“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并在1976年联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公司筹集720亿日元(2.36亿美元),设立“VLSI技术研究所”,开启了一场蔚为壮观的、针对DARM存储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目前最常见的系统内存)的大攻坚。
昭和一代的日本名企展现出了空前的团结,攻坚体系由6大实验室组成:
日立(第一研究室)负责研制电子束扫描装置和微缩投影紫外线曝光装置;
富士通(第二研究室)负责研制可变尺寸矩形电子束扫描装置;
东芝(第三研究室)负责研制EB扫描装置与制版复印装置;
电气综合研究所(第四研究室)负责对硅晶体材料进行研究;
三菱电机(第五研究室)负责开发制程技术与投影曝光装置;
NEC(第六研究室)负责进行产品封装设计、测试、评估研究。
对一些关键技术难点,日本各公司像《流浪地球》里对地球发动机的饱和式救援一样,开启了“饱和式攻坚”:多个实验室群起而上,以各单位的竞争保证研发成功率。
VLSI成果惊人,计划开启第4年(1980),在惠普对16K DRAM内存的竞标中,日本的NEC、日立和富士通完胜美国的英特尔、德州仪器和莫斯泰克(当时美国存储器领域最主要的玩家),美国质量最好的DRAM的不合格率比日本最差的公司还高6倍。
VLSI开始的第6年(1982),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生产国;
VLSI开始的第9年(1985),NEC登上全球半导体厂商榜首(按收入),并在之后连续7年稳坐头把交椅;
同年,被日本厂商压着打的英特尔关闭了7座工厂,裁员7200人——这家11年前市占率达80%的公司从此关闭了存储器业务。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1970年,还悄悄发生了另一件小事:年初,一家日本计算器公司Busicom给了英特尔一个单子——做一款定制芯片的设计和生产。
Busicom最初的方案是一套由12块集成电路组成的系统;而英特尔工程师Ted Hoff看了后觉得太复杂,他创新地提出,可以把计算单元集中到一枚芯片上,以简化电路和降低生产成本。
正是在这个项目中,英特尔开发出了于1971年面世的Intel 4004,这是世界第一枚商业化的微处理器,即CPU——当今半导体产业的桂冠明珠。
Intel 4004最初的广告:“宣告一个新型集成电路时代”
Busicom的订单起初并不被英特尔重视。
70年代,英特尔和它的竞争对手日本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存储器上,英特尔创始人,时任CEO罗伯特·诺伊斯甚至说过:
“CPU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英特尔有能力做,但是脑子坏了才会真的去干。卖CPU的话,每台电脑只能卖一块,我们现在做内存,每台电脑能卖几百块芯片。”
可谁能想到,偏偏这个不受待见的新业务,在之后力挽狂澜。
新兴的CPU业务如出笼猛兽,带领英特尔于1986年、1993年、2002年、2010年创下4次业绩高峰——英特尔不仅起死回生,还发展成日后的半导体常青树,成就了如今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中的话语权。
在转型CPU后,英特尔“王者风范”初现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是日本的“有心追赶”,还是美国的“无心插柳”,背后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全球商贸合作、产业分工的受益者。
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贸易全球化和技术交流,日本难以在最初引进半导体先进技术,也就没有日后赶超的基础;美国也难以在服务全球产业需求的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找到大有前景的CPU“边缘市场”。
半个世纪过去,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一个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已在眼前。
站在“中国芯”的拐点上,两种观点正互相争锋:
一种颇有市场的声音是:另起炉灶,全产业链自己干。
在AMD等厂商被传停止向中国授权新一代x86架构IP(IP是芯片可复用的逻辑单元,是芯片设计最核心的部分)等新闻后,就有大量对中国“承包半导体全产业链”的遐想:
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以中国现有的技术实力,不能“狭隘地”自己闭门造车。
如任正非日前接受采访时所说:
“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美国公司现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批,如果审批通过,我们还是要购买它,或者卖给它(不光买也要卖,使它更先进)。因此,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
是从最底层开始重建一遍,还是继续拥抱全球分工?
抉择时刻,同样作为半导体产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日、韩、台“崛起史”,为中国大陆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回顾历代后来居上者,其共性是:遵循科技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站在全球分工、技术合作的基础上,敏锐抓住并卡位新一波周期或新市场机会。
第1次拐点:产业转移,日本超美
作为在美国之外,最先从半导体市场分得一杯羹的国家,日本顺势而为的方式是:
在外部条件有利时,不断引进技术,获得存储器领域的绝对优势。
乘着战后美国“援日抗苏”的有利外部条件,日本从50年代开始以低价获取了大量美国技术的授权。
1953年,日本“东京通信工程株式会社”在晶体管专利被受理仅5年后,以900万日元(约2.5万美元)的低价从西屋电器引进了晶体管技术——要知道肖克利最初研发晶体管时,贝尔实验室在其上连续砸了2.23亿美元(用于1948年~1957年的连续研发和优化,其中美国军方承担了近40%的费用)。
借助晶体管技术,东京通信在1955年发布了第一款袖珍收音机TR-55,公司也正式更名为索尼。“索尼大法”由此发扬光大,成就一代传奇电子企业。
当时,去纽约与西屋签约的索尼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在逛了帝国大厦、布鲁克林大桥后,曾向同行友人感叹:“日本和这样的国家交战,真是鲁莽呀!”
不过20年后,日本就在半导体存储器领域和美国打了一场惊人的大战,这得益于日本在60年代引进的另一项技术:集成电路。
日后成为日本半导体霸主的NEC,在1962年从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购买了平面光刻生产工艺,解决了集成电路制造生产的问题,效果立竿见影:1961年,NEC集成电路的产量只有50块,1962年暴增至1.18万块,1965年达到了5万块。
同一时期,日立与RCA,通用电气和东芝纷纷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索尼和德州仪器也在历经4年磋商后,于1968年在日本成立了各自占股50%的合资公司。
日本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套路,成立合资公司的条件就是德州仪器必须在3年内向日本公布与IC制成相关的专利。
于是,外有“向先进学习”的敏锐抓手,内有举国体制下的“VLSI计划”,这一系列举措,打下了日本在70年代埋头苦干、80年代一鸣惊人的基础。
从1980年到1984年,日本半导体对美国的出口额从不到90亿日元,增至400多亿日元,陡峭的上扬曲线震动世界。
1985年的出口量下降与美国启动针对日本存储器的“反倾销诉讼”有关
由此,日本成了半导体史上的第一次“产业转移”的赢家,夺得了存储器市场的垄断地位;而美国顶尖公司如英特尔,则转向了技术壁垒更高的CPU领域。
不过,日本半导体的辉煌是短暂的。
9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开始节节败退——韩国成了新一代存储器霸主:1992年,三星将NEC挤下DRAM世界第一的宝座;2000年前后,富士通和东芝先后宣布从DRAM市场退出。
这背后有诸多原因:在外,美国像如今对付中国一样,对日本耍起了“贸易战”:通过1985年的反倾销诉讼、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1991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全面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内,日本在80年代末达到泡沫经济顶峰,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减少了对技术领域的投资。
而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原因是,日本错失了一个萌芽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新趋势。
这一回合,台湾和韩国却抓住了机会。
第2、3次拐点:分工裂变,韩、台逆袭
台湾和韩国逆袭的故事,源自一场涉及美、欧、亚多国的半导体行业“分工裂变”。
一切的开端仍是不起眼的小事:诞生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家小公司——台积电和ARM。
成立于1987年的台积电开创了Foundry模式,即只进行芯片生产制造的芯片代工厂。而3年后,诞生于英国剑桥一座谷仓里的ARM,又开创了另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IP授权。
Foundry和IP授权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
从集成电路商用化的60年代开始,半导体产业就像细胞生长一样经历着“裂变”——从垂直集成到垂直分工,分工越来越细,各环节越来越专业。
第一次重要裂变发生在70年代:半导体和软件行业从计算机中分化出来。
行业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公司造所有”的高度垂直集成。比如IBM蓝色巨人,既自己造计算机用的芯片,还做操作系统、软件,同时生产计算机终端。
在1961年底IBM启动的“System-360”项目中,凭一己之力,IBM就攻克了指令集、集成电路、可兼容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软硬件多道难关,获得了300多项专利。
而到70年代,随着技术进一步普及、市场对软件需求的增加,软件开始成为单独的行业;微软(1975年成立)、甲骨文(1977年成立)等公司陆续出现。
这同时催生了半导体从计算机中分化,产生了一批主要做芯片硬件(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公司,英特尔(1968年成立)是其中代表。
在1970年代开始萌发的PC(个人电脑)市场上,英特尔与微软的“Wintel联盟”悄然生长,前者做计算机CPU,后者做Windows操作系统,软硬配合,逐渐获得了垄断地位。
这又带来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重要生态现象:指令集壁垒。
有种说法是:三流公司做产品,二流公司做品牌,一流公司做标准。指令集,就是芯片硬件和底层软件代码之间沟通的一套“标准”。
就像只有灰姑娘能穿上水晶鞋:相应的软件操作系统,通过相应的指令集跑在相应的芯片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指令集和操作系统之间能形成其他玩家难以攻破的生态联合。
随PC浪潮崛起的英特尔,是第一个创建起了“指令集壁垒”的公司。
PC时代之前的小型机主要在数据中心处理专业的计算工作,市场分散,操作系统常常是各做各的(或在开源系统上做优化),井水不犯河水;指令集也各自为营,IBM有Power,Sun有SPARC,DEC有Alpha等等。
随着PC时代到来,大量个体沟通、协作的需求开始涌现,操作系统市场开始向头部玩家集中,Windows最终突出重围,坐上了“铁王座”,与之绑定的英特尔x86指令集也跟着取得“指令集霸权”。
2000年之后,英特尔又进一步利用自己在PC市场出货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向更高端的“小型机服务器市场”进军,以价格战打败了Power、SPARC、Alpha等老牌指令集,改写了整个服务器市场的生态基础。
对x86指令集这一电子产业基础性标准的掌控,也让英特尔多年来屹立不倒,连续25年(1991-2017)登顶全球半导体第一厂商的宝座。
这便是行业第一次裂变时,新一代“软硬双打”撂倒老一代垂直型巨人的故事。
但在芯片制造内部,英特尔仍是一家“垂直集成”的公司:自己做指令集,自己在指令集上设计IP核,自己做生产制造。
这就给第二次分工裂变创造了空间: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台积电的Foundry模式+ARM的IP授权模式兴起,打碎了英特尔的“垂直集成”。半导体产业上游的IP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制造各自分化成了单独的行业。
ARM能产生IP授权的奇思妙想,也得感谢英特尔。
1981年,ARM的前身Acorn计算机公司想生产一款供英国中小学校使用的电脑,向英特尔求助,希望能购买80286处理器的设计资料和样品,但英特尔没搭理它。
Acorn于是基于当时学界提出的RISC精简指令集概念(英特尔x86使用的是CISC复杂指令集),研发了一颗32位、6M Hz,使用自研指令集的处理器,命名为ARM。
到1990年,已更名为ARM的新公司开始专注于半导体业务。但英特尔等厂商已占据了大量市场,直接卖芯片的ARM生意惨淡,被迫踏上一条新路:自己不生产芯片,只将IP核授权给其他公司。
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台积电的成功则得益于其创始人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积累的半导体工厂建造与管理经验。
与开头提到的日本通过引进技术发展存储器;英特尔因为完成日本客户订单阴差阳错开启CPU市场一样,全球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再次促进了整个产业的进化。
进化是不可逆的。
Foundry和IP授权模式的诞生,永久地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版图——它大大降低了半导体产业的准入门槛。
在高度垂直集成的60年代,IBM为开发System-360,在3年多时间里投入了52.5亿美元,开支甚至超过造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力雄厚如IBM也差点被这个项目搞得资金链差点断裂,其他小厂家更是被完全挡在了电子产业的门外。
随着垂直分工的开始,ARM和台积电承担了产业链一头一尾的工作,中间的“芯片设计”环节便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赛道——不做生产,无需重资建厂或做底层研发的Fabless厂商(Fabless的字面意思就是“无工厂”)。
目前全球排名Top 20的半导体厂商中,近一半是1990年后成立的Fabless新贵:
1985年成立的高通(美国)(高通是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商,1994年开始销售芯片);
1991年成立的博通(美国);
1993年成立的英伟达(美国);
1995年成立的美满(美国);
1995年成立的联发科(台湾);
1999年独立的英飞凌(德国)(前身是西门子半导体部门);
2002年成立的瑞萨电子(日本)(NEC和瑞萨科技的合资公司)。
这进一步给行业带来两个变化:
一方面,更多轻资产玩家的涌入,使市场竞争更充分,促进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进化;
另一方面,这些新公司多是ARM和台积电的客户。ARM以开放的IP授权模式已在移动端CPU市场占比超95%,与服务器端CPU的霸主英特尔屹立两头,构成了当下全球半导体产最底层的两大标准。
这场新的分工裂变,终于让高端的CPU领域不再是“美国人自己的游戏”,台湾和韩国顺应新的分工趋势,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新高地。
在制造环节,台湾依靠台积电牢牢把握了话语权。
自从在1989年搞定了英特尔的背书和订单后,这家最初连募资都很艰难的台湾“小公司”快速成长,每年营收增长率都保持在50%至100%之间。
近年来,台积电的工艺水平已赶超了传统垂直厂商英特尔、IBM,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在最新的5nm制程上领先全球。
在CPU、MCU等主控芯片设计环节,另一家台湾企业联发科从2003年开始购买ARM IP,进入手机和平板芯片市场,并在2000年之后成为亚洲最大的Fabless厂商。
韩国也抓住了分工裂变的机会。
其半导体标杆企业三星,从2000年开始就通过购买成熟IP,在原本的强项存储器之外,开辟了CPU的新增长点。
2007年,第一代iPhone的芯片就是三星和ARM分工合作的产物——三星在ARM 11 IP上开发的S5L8900芯片。
谁能想到,iPhone这个不被看好的“边缘产品”,一手撑起了智能手机时代,在推出后第二年,创下了超过700%的销量增长。
乘此东风,三星巩固了其在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的地位;随后又在2010年推出蜂鸟系列CPU(后改名Exynos),奠定了其在Android设备阵营的龙头芯片提供商地位。
其实,中国大陆的许多公司也在不知不觉中赶上了行业分工裂变的大势。
由于“IP授权+Fabless+Foundry”模式降低了手机芯片整体成本,国产手机厂商,如华为、小米、vivo、OPPO在2010后崛起,成了这场绵延近30年的新分工潮流的受益者。
这就是全球产业链的神奇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起初看来微小的变化,经时间陈酿,可能孕育巨大的机会。
但是,“势”能助人也能伤人:如果你要和它对着干的话。
在韩国、台湾崛起的9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败落,原因之一就是错过了垂直分工裂变的趋势。
当时,日本的优势项存储器遭美国狙击,并被韩国趁虚而入;但在CPU领域,日本本可与IP授权商、晶圆代工厂合作,发展Fabless业务,再一次“后发制人”。
但日本公司在90年代还瞧不起技术相对落后的台湾代工厂;另一方面,正如日剧《半泽直树》所展示的,日本的实业融资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在评定资产时,倾向于工厂、生产线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单独的芯片设计公司不好找钱。
于是,保持着垂直集成形态的日本半导体企业既要研发,又要生产,还要维护、更新设备,投资大,周期长,技术更迭落于Fabless之后。
在发现市场新机会上,自由、灵活的小公司往往更有潜力,团结大公司一起攻坚的日本模式此刻反而成了短板。
在美国的打击和Fabless模式的双重挤压下,日本半导体丢掉了旧优势,错失了新的增长机遇,只留下“失去30年”的叹惋。
回看这段历史,冲击垂直集成的两大角色——台积电和ARM都诞生在腹地狭小的岛屿,这有其必然性:
正因内部市场有限、地理位置边缘,台积电和ARM才“光脚不怕穿鞋”,各自发明了全新商业模式。借承担新的分工角色之机,它们既实现了自身的商业成功,也共同促成了一个更开放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
万一,2019年的半导体仍是一个被美国少数巨头把持的产业,那中国会面临什么局面?
想都不敢想。
南北殊途:大陆半导体探索
在IP授权+Fabless+Foundry分工诞生10年后的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成了加入半导体产业商业竞争的最新玩家,续写着这部全球分工大戏。
与如今一样,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让中美关系跌至冰点。
传导到半导体产业,出现了对全球分工态度迥异的两派实践。
一边是“全部自己来”的北派。
它们多脱胎于学术机构,在2000年前后集中出现:
1999年,方舟成立(倪光南院士与市场化公司方舟科技的合作);
2002年,北福斯志成立(2001年北大众志对应的实验室MPRC成立);
2008年,龙芯成立(课题组成立于2001年,2008年公司成立)。
另一派是接地气的南派,由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企业组成,其成立高峰期同样在2000年之后:
2001年,展讯成立(2013年紫光收购展讯,2014年又收购锐迪科,2016年集成为紫光展锐);
2001年,炬力成立;
2001年,瑞芯微成立;
2004年,澜起科技成立;
2004年,海思成立(华为子公司);
2004年,兆易创新成立;
2007年,全志成立。
在发展路径上,北派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双重目标:既要完成国家重点任务——在当时中美不睦的大环境下,攻克自主可控的CPU,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要通过成立公司,探索市场化。
这就不难理解,龙芯、众志都选择了一条最凶险的路:从最上游的指令集开始,一层层往下游做,构建自有体系,挑战CPU高地,试图捅破Wintel联盟,不做底层技术有求于人的“买办芯片公司”。
如北福斯志,先后在1999年做了完全自主研发的指令集及架构UniCore,又在2003年做出了包含UniCore核的PKUNITY-863 CPU;龙芯趁2008年金融危机,低价获得了MIPS指令集授权,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扩展,发展出了自己的指令集LoongISA;方舟则通过做嵌入式的RISC类型指令集,绕开x86的垄断,在2001年推出了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研发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
南派的共通点则是完全融入全球分工,从最没技术门槛、最下游的买现成芯片做起,一层层往上游和底层“洄游”。
20年弹指一挥间,暂且不表培养人才、支持军工等特殊领域的进展,仅在产业化上,两种相向而行的路径,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架构决定生态,无论是完全自主研发还是基于MIPS指令集扩展,绕开了x86的北派——龙芯、方舟、北大众志,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芯片,却补不齐生态短板。
正如梁宁在去年中兴事件后广为流传的《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中所写: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英特尔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
敌不过Wintel联盟,北派深陷于市场化泥潭。
它们曾通过自己做办公软件、甚至配套硬件来闯出一条路:
如众志推出了与PKUNITY-863 CPU适配的操作系统(基于开源的Linux),并进一步推出了使用PKUNITY-863的“网络计算机”(要连网才能使用各种应用的电脑,起初具有成本优势,但很快在价格上被更强大的产品碾压);方舟也做了可更好适配自有芯片的永中Office套件和NC瘦客户机(一种网络计算机)。
这几乎回到了60年代,IBM的“高度垂直集成模式”。
但IBM这么干时,微软、英特尔还不知道在哪儿;中国半导体北派这么干时,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已是巨头林立。
结果不难想象:这些一体化的产品在好用、便宜的Wintel联盟面前并无战力。
最终,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龙芯和众志则主要在军工等领域获得政府订单,但仅从收入上,在大陆范围内也难以跻身头部厂商。
而南派的打法却很“接地气”——从低端到高端,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演进,形成了多层次的商业进展。
南派中的第一种是,紧跟市场需求,什么赚钱做什么。
比如在MP3产品大行其道的2005年前后,珠海炬力凭借MP3芯片(多媒体影音主控芯片)获得了快速发展,在2005年出货7000多万颗,销售收入突破1.5亿美元,并在第二年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MP3芯片厂商。
2010年前后,瑞芯微和全志又后来居上,进军平板市场,早早开始购买ARM IP研发平板CPU,成了当时南派中的新一代佼佼者,客户也从国内厂商逐渐变为惠普和谷歌(chromebook)。
海思则属于另一类:主要服务于华为的战略目标,做与通信紧密相关的交换机芯片、基带芯片;并在近年随华为手机业务的发展,开始挑战高门槛的移动端CPU,成了近7年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的收入冠军。
最近10年来,排在中国Fabless厂商前10的多为南派厂商。
南北殊途、结果迥异,是因为对全球分工的不同态度;态度差异源于,是否清醒地承认行业发展的规律和现状:
经过50多年的积累、发展,这么多公司的生死起伏,半导体产业已形成了专业、细致的分工,一环扣一环的合作体系,和短期内难以打破的生态配合。
PC时代是Wintel联盟横扫天下;移动时代则形成了ARM+iOS、Android对下游芯片和终端厂商的强大话语权。
中国作为半导体技术和商业化上的后发选手,尤其是在技术门槛最高的CPU领域,即使国内市场庞大,也很难自成一派,去与物美价廉、生态成熟的国际芯片产品硬碰硬。
在“甲子光年”去年关于国产自主CPU之一北福斯志的文章《北大理科一号楼芯片往事》中,提到了中国半导体“不融入全球分工”的一种可能性:让国家给一片“小市场”。
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在黑暗森林里围个篱笆墙,构建一个小森林,“把国外芯片挡一挡”;让真正自主可控的中国CPU在小森林里按市场规则竞争,再让胜出者去和黑暗森林里的国外产品竞争。
但即使是在国家看起来可以控制的政府办公、国企办公、教育领域,当市面上的CPU比国产CPU性能更高、价格更低时,让部门牺牲利益支持国产,仍有巨大阻力。
如2014年云计算兴起后,众志曾拓展“桌面云”业务,并拿到了国家电网的一张大单,背景是当时国家电网认为用个人电脑办公不安全,下令不再采购电脑,而改用桌面云,由服务器端统一管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桌面云对娱乐软件和部分外设硬件支持不好,基层办公人员还是不愿意变——不让买新电脑了,有的分公司就去租电脑,这次合作也不了了之。
靠划出一片“温室市场”的做法,不一定能扶起产业。这就像人类模仿生物圈建造的“生物圈2号”——它是一个壮丽的实验,却终究是一场惨烈的失败。
匍匐向前:海思的自研之路
在自成一体的“生物圈2号”之外,从2005年到2018年,浸泡在市场化竞争里的南派芯片公司,经历了激烈的排位重洗,各公司被逼迫着向更高端、更有门槛的产品、更新的细分市场或更深程度的自主研发演进。
其中,近年来表现最亮眼的华为海思提供了一种“三步走,依次上台阶”的路径示范。
这种依靠国际分工的已有成果,“站在巨人肩膀”上缓慢“匍匐”的战略,再次证明了一个产业发展心法:慢即是快。
第一阶段是1991年~2004年海思成立前。华为有两手做法:
在不需要IP和通用指令集的专用芯片,如交换机用的ASIC(专用集成电路)上,华为采取了冒险的自研。
当时,华为创立不到5年,这家甚至倒卖过减肥药的公司最后把业务稳定到了代理PBX交换机上。在看到了中国市场对交换机的旺盛需求和当时的混乱标准后,任正非开始组织自研团队,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研发交换机用的ASIC。
任正非说动了自动控制系研究生徐文伟,从隔壁的港资企业跳槽到了当时前途未卜的华为。徐随后带领团队在1991年和1993年研发了SD502和SD509;这些芯片使华为自研的交换机比其他使用通用芯片的厂商更便宜,华为也由此从商贸公司转型科技公司。
为了芯片研发的资金,任正非当时甚至借了高利贷。
他曾站在六楼办公室窗前,对研发团队说:“新产品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
而对于需要依托于指令集的CPU、MCU等芯片,华为采取了直接购买现成芯片的方式,如在数据中心中使用了大量的英特尔 CPU。
第二阶段是2004年~2018年,华为海思成立,仍然分两手:
一边继续优先研发与华为的通信业务密切相关的专用芯片ASIC;一边从直接购买现成芯片,进化到了购买IP,进军移动端CPU市场。
最初的尝试是2006年开始研发的K3V1嵌入式CPU,该CPU基于ARM-11 IP,被集成于海思公司的首款手机主芯片Hi3611上,但由于性能问题,K3V1最终没有市场化;此后,海思闭关两年,推出了K3V2处理器,并且第一次在自家旗舰机型D2、P2、Mate 1、P6等手机上使用。
到2014年,华为又推出了麒麟920芯片,并在华为荣耀6上使用。这款芯片集成了8个ARM核和华为自研的基带芯片巴龙,获得了当时的“跑分王”之称。
这是海思成立的第8年,华为开始自研芯片的第23年,华为海思终于在移动终端CPU芯片上有了看齐高通、三星等一线厂商的实力。
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海思从购买现成的IP又进化到购买ARM指令集架构,开始基于架构进行更深度的自研:
这款深度自研的产品是今年1月发布的服务器端CPU泰山芯片,它将部分替代英特尔的服务器芯片,大大降低华为运营数据中心的成本。
至此,海思成了中国第一家成功基于ARM架构自研并量产了CPU核的厂家。
其实,这三步走就是老老实实顺应产业发展规律,走日、韩、台的后发者们都走过的路:积极利用全球分工体系,引进已有技术成果,稳扎稳打,逐步从下游切入上游,从浅层自研走向深度自研。
这种顺势发展的关键是承认以下现状:
以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的技术实力,无法完全抛开全球分工体系;即使大陆最先进的厂商海思,在移动端CPU上还是没有自己做到最底层的指令集;同时,还得依赖美国的EDA工具(EDA是芯片设计中的后端实现工具,它能把芯片设计翻译成工厂能看懂的制造流程)。
这就是为什么,在BBC爆出ARM内部受美国影响,可能不再与华为进行新一代ARM架构合作时,中国半导体产业一时舆论沸腾。
但实际上,悲观情绪背后有两个少为人道的有利信息:
首先,华为已购买了ARMv8架构的永久授权,继续用着没问题。
其次,“甲子光年”从接近ARM的人士得到的消息是,美国的禁令只对在美研发占比超25%的ARM技术和产品有实质约束;而ARM所有的指令集核心IP和大部分内核IP都属于“英国或欧洲原产技术”,受美国禁令影响较小。
ARM创始人Hermann Hauser近期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也说:
“封杀华为最终会对ARM、谷歌甚至美国工业带来严重伤害;一些欧洲公司已在考虑将美国IP产权排除在外,或与美国子公司、办公室做一定程度的切割,以免日后自己的生意受美国禁令波及。”
如果这种态势进一步发展,特朗普就真的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可能会失去部分的欧洲技术资源,这对几百年来以汇聚人才和技术为傲的美国来说,是动摇根基的打击。
作为这一轮摩擦的挑起方,美国给中国,也给自己和全球造了一个新的“势”,它也不得不受新“势”的反噬。
第4次拐点:顺势而为
明势、取道、优术,事可成。从近几十年的沉浮故事来看,“势”便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今的半导体产业,面临第四次拐点。三个“势”摆在历史的分叉口面前:
长期的势是全球分工和技术交流趋势难以阻挡。
到今天,全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半导体全产业链的自给自足。
面对半导体这种日益复杂、精密的行业,汇聚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垂直分工更有利于行业的整体发展。
另一方面,参与半导体棋局的各国和地区已在大分工体系中找到了各自的立身所长:
美国半导体产业强在整体实力:
有英特尔、高通、英伟达、AMD等顶尖芯片设计、制造厂商,英特尔、AMD还掌握x86指令集
有微软、苹果、谷歌等操作系统生态伙伴
有Cadence、Synopsys、Mentor 3大主流EDA工具厂商
英国强于架构:
有除x86之外,占据另外半壁江山的ARM架构
台湾强于代工:
台积电在先进工艺上已领先世界
韩国强于存储和显示:
三星和LG在9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
日本强于材料:
信越、SUMCO、住友电木等日企垄断全球52%的半导体材料市场
欧洲强于设备:
荷兰ASML公司垄断全球光刻机设备
而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地,在产业链上是最大的芯片组装地;近年来,中国大陆Fabless行业也有快速发展,2018年的Fabless广商总量已是2010年的3倍。
所有参与产业链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希望看到分工合作由开放转为封闭。因此在这个“势”上,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立场接近,站在有利位置,有一定周旋空间。
短期的势是美国可能升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继ARM之后,AMD也在这几天登上科技头条,AMD官方已确认,不再向其中国合资公司天津海光授权基于新一代x86指令集的IP。
而在中国北派芯片公司挑战未遂、南派公司尚未涉足的指令集层面,目前全球市场的主流玩家不多:
美国英特尔、AMD的x86指令集——服务器、PC端的主流指令集;
美国IBM的Power指令集——服务器、PC端的指令集;
英国ARM的ARM指令集——手机、平板等移动端的主流指令集;
美国RISC-V基金会开源指令集RISC-V——目前主要用于物联网设备。
英特尔向来不对外授权x86架构,而主要用于自有芯片;AMD已因合规问题主动规避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RISC-V产业联盟理事长、上海芯原微电子董事长戴伟民在5月底也对外表示,美国RISC-V厂商已不能向华为出售IP。
还好,在移动CPU和服务器CPU市场,英国ARM是“硕果仅存”的“非美国货”,且2018年5月,ARM和中国资本合资,成立了中资占股51%的ARM中国,这有利于推动国内芯片企业掌握ARM核心技术。
同时,ARM中国对自研的产品(如去年推出的AI IP周易等)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受任何其他地区的影响;这将为中国芯片研发进一步国产化、底层化带来机遇。
此外,基于开源指令集RISC-V的IP虽已被禁售,但RISC-V本身作为一套开源标准尚未受到禁令的明确影响;虽然RISC-V目前主要用于物联网芯片,5-10年内都无力支撑移动端CPU和服务器端CPU市场,但它可能给物联网厂家带来机会。
在美国内部,谷歌、英特尔等公司被报道正在游说美国政府,争取获得当前禁令的豁免权,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是维护全球供应链合作的另一种力量。
因此,对中国不利的第二个“势”——即美国的严厉技术封锁,以更长的历史周期看,可能是相对短期的扰动。
就像上周“甲子光年”发布的《甲小姐对话吴军:人的归人,机器的归机器》中,吴军博士提到的:
世界上有四种力量是自由流动的,一是技术,二是资本,三是人才智力,四是信息——你在一个地方拦住它,它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会过去,所以很多时候危机就是机会。
全新的势是:AIoT新机会。
历史上,每一代半导体新巨头和新兴地区的出现都伴随着终端迁移:PC市场成就了英特尔;移动市场成就了ARM、高通、三星、台积电;而在“AI+物联网”(AIoT)的新机会中,中国厂商很可能脱颖而出。
中国也在近年诞生了一大批AI公司、芯片公司,有泡沫,也有真金沉淀;中国还有大量的智能化市场需求。一些有资金、技术、经验积累的中国厂家,甚至已开始了对最底层的攻坚。
这一次,已经在市场化大潮中摸爬滚打十几年的中国公司,真的有机会像NEC抓住存储器,高通、三星抓住智能手机芯片一样,后发制人,真正切入高端和上游。
综合看目前的形势和过去数年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全球化分工是“民心所向”;贸易封锁是短期扰动;新的硬件迁移机会是产业机遇。
1956年,中苏出现裂痕,毛泽东曾在当年会见拉美国家党代表时说:“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
在趋势和外部环境有利有弊,搅入如今局面的各国并非铁板一块的情况下,明智的抉择尤为重要。一切自己来,实现全产业链的自给自足,说起来豪气干云,但并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更尊重事实的认知是,ASML、ARM、台积电等尚可做朋友的非美国公司短期内无法被取代,特别是在移动端和服务器CPU领域,中国仍需要全球合作伙伴的支持。
退一步讲,即使出于战略考虑,中国在不计性价比地“重复造轮子”后,真做到了不怕“断供”,我们也应该和多数国家站在一起,推动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因为一个相互羁绊、紧密依存的全球贸易体系既能促进全球科技产业以更高效率进化;也让世界更彼此需要、彼此依存,让各国在“一时上头”时会更有挂碍。
相反,一种鼓吹中国已实力强大,可以接受封闭体系的言论则有危险性。
如中微半导体设备董事长尹志尧就曾痛斥有关他的报道《此人突然回国,美国慌了,日本傻了,世界都惊呆了》是“科技义和团”:
“对我和中微的夸大宣传,搞得我们很被动。
……
如此堕落的文风误国误民,给真正埋头苦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添堵、添乱、添麻烦。你们的义和团式博眼球行为,只能阻碍甚至害死发展中的中国高科技,这么点道理都不能懂吗?”
真正的赶超姿势可能十分朴素:沿着全球分工和硬件迁移的产业发展路径,不会的要承认,该学的要学,该抓住的要抓住。
时间会站在顺势者的一边。
参考资料:
1. U.S.-Japan Strategic Alliance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Competiton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on Japa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 D.C , 1992
2. 半导体行业资讯:《回顾美日DRAM芯片之争》
3. 兰涛:《创新源自洞见:盛田昭夫的商道公开课》,2012,中国华侨出版社
4. 小托马斯·约翰·沃森、彼得·彼得 著,杨蓓 译:《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2015,北京联合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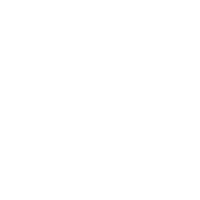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